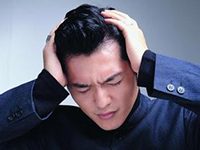脑损伤后痉挛状态(肌张力增高)治疗进展
痉挛状态[1,2],即由于脊髓节段牵张反射亢进导致的速度依赖的被动活动肌张力增高、腱反射亢进、阵挛和肌肉强直,是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后致残的重要原因,见于脑卒中、脑外伤、脊髓损伤、脑瘫、多发硬化等疾病。据一篇英国文献报道,全世界约有1.2亿人受痉挛的影响,仅在英国就超过10万人,其中半数以上的痉挛需要治疗。一直以来,临床医生对于痉挛的普遍性和危害性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随着康复医学的快速发展和广泛普及,痉挛的预防、诊断和治疗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北京博爱医院神经外科张新
痉挛是神经网络损伤后失协调或(和)过度代偿的结果,实际上它不仅累及躯体运动系统、还涉及内脏运动、甚至躯体感觉、内脏感觉等系统。Brunnstrom的上运动神经元损伤后阶段性恢复理论认为伤后肌张力由弛缓逐渐过渡为异常增高具有必然性。适度的肌张力是维持协调运动的基础,然而过度增高的肌张力却又是严重阻碍神经功能恢复的重要因素。痉挛可以累及全身各处的骨骼肌和平滑肌、原动肌和拮抗肌,这种严重失协调可以引起全身广泛功能障碍[3]。如眼外肌痉挛表现为目光呆滞、眼球协调运动障碍;面部肌肉痉挛表现为面容凝固、表情单一;咽喉肌肉痉挛表现为言语笨拙、发音不清、交流障碍、吞咽困难、饮食呛咳、误吸;四肢肌肉痉挛表现为关节活动障碍、疼痛、运动控制及协调能力下降;膀胱逼尿肌、括约肌痉挛表现为尿频、尿失禁、尿潴留等。痉挛导致疼痛、压疮、肌肉挛缩、关节变形、关节脱位、病理性骨折及上述情况所致心理障碍等广泛影响患者器官功能的恢复、是导致日常独立生活能力下降、残疾程度提高的重要因素,也是目前临床上脑功能治疗和康复的重要内容。
痉挛治疗的常见目标包括改善身体器官功能、提高日常生活独立能力,如改善关节活动度、释放受拮抗的肌力;减轻疼痛;增加矫形器佩戴的合适程度,改善矫形位置,提高耐力;改变强迫体位、改善体位摆放,改善舒适度;预防和减轻与痉挛有关的并发症,如肌肉和关节挛缩,延迟或避免外科矫形手术;消除有害的刺激因素,预防压疮或促进压疮愈合,使护理更容易、减轻照顾者的负担。
对于痉挛的病程、部位、程度、痉挛关节肌肉骨骼受累情况、疼痛情况、合并症、日常生活能力、心理状况等全面进行评估,制定适合的康复目标与治疗方法。[4,5,6]目前临床上防治痉挛主要有运动疗法、理学疗法、生物反馈疗法、口服抗痉挛药物、鞘内持续注射抗痉挛药物,肉毒素注射,外科手术治疗(包括选择性脊神经后根切断术、外周体神经切断术、脊髓局部传导束切断术)等。口服抗痉挛药物主要为神经递质抑制剂,在缓解肌张力的同时也抑制和改变了诸多高级神经功能,如认知、警觉性、情绪等,并且疗效有限、易产生耐药性等。运动物理疗法是利用力学原理,借助器具、徒手等方法及电、光、声、磁、温度等物理因子进行治疗,作用有限、显效慢、不持久,多用于痉挛的预防阶段。肉毒素注射受其注射总剂量限制而不适用于大关节部位的肌肉痉挛,且有明显的肌无力副作用、又因其半衰期短而疗效持续时间有限[7]。鞘内注射法疗效确切、注射药物用量小、副作用小,但因受治疗部位限制、有异物置入术相关并发症,加之材料费、术后维护费昂贵等弊端临床应用受到限制。
痉挛的部位和程度是临床上采取何种治疗措施的决定因素,严重性的痉挛占有重要比例,痉挛的病理模式一旦产生,会逐渐泛化、加重,并且形成恶性循环。实践表明选择性脊神经后根切断术(Selective Posterior Rhizotomy, SPR)是目前治疗严重痉挛最为理想的手段。[2]1908年Foerster提出脊神经后根切断术治疗痉挛状态,继之于1967年Gros等将其改进为选择性脊神经后根切断术,并得到推广。1976年Fasano等人又将其改进为以后根电刺激为依据的改良Foerster手术,并称其为超选择脊神经后根切断术。数十年临床实践证实SPR术后有很好的远期效果,Khalil报道154例患者随访10年疗效保持率达90%[8]。SPR手术后无切除神经根支配区的浅感觉障碍及肌力下降的不良副作用,选择性、限制性椎板切除及椎板复位成型固定等技术避免了术后脊柱结构不稳的并发症,目前正在开发的内镜下手术操作将进一步提高微创。实质上SPR术是一种通过外科手段来实现神经调控的一种技术。虽然SPR手术是一种毁损性手术,但因其疗效确切持久、医疗花费少,随着微创技术不断改进和提高,获益风险比值显著增高,逐渐成为严重痉挛的理想治疗方法。我院神经外科多年来临床实践显示SPR术后痉挛100%得到改善,并且令我们更加鼓舞的是我院神经外科脑损伤后痉挛性瘫患病例实施SPR术后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手术节段以外的正面效应。例如选择性切断腰骶段脊神经后根后不仅下肢痉挛得到缓解,并且双侧上肢痉挛也得到缓解、语言流畅性得到改善的效应。
我院神经外科多年来在脑外伤、脑出血后痉挛性瘫痪的肌张力增高的病因诊断、治疗方案的选择、判断预后、指导康复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参考文献]
[1]姚泰.生理学[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475-480.
[2]卓大宏.中国康复医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676-698.
[3] Brainin M, Norrving B, Sunnerhagen KS, et al.Poststroke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towards improved identification and interventions for poststroke spasticity-related complications.Int J Stroke. 2011 Feb;6(1):42-46.
[4]Dones I, Nazzi V, Broggi G.The guidelin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spasticity. J Neurosurg Sci. 2006 Dec; 50(4):101-105.
[5] McLaughlin J et al. Selective dorsal rhizotomy: meta-analysis of three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Dev Med Child Neurol 2002; 44: 17-25.
[6]Boop FA. Evolution of the neurosurgical management of spasticity.J Child Neurol 2001;16:45-57.
[7]Ward AB.Spasticity treatment with botulinum toxins. J Neural Transm. 2008; 115(4):607-616.
[8]Khalil Salame MD, Georges E.R. Ouaknine MD, Surgical Treatment of Spasticity by Selective Posterior Rhizotomy:30 Years Experience. IMAJ . Vol 5 . August 2003.543-546.
- 上一篇:脑挫裂伤的治疗
- 下一篇:脑损伤后记忆障碍的康复治疗
相关文章
- 脑外伤的治疗办法
- 中医如何治疗脑外伤
- 脑外伤癫痫可不可以手术治疗
- 脑外伤的恢复治疗
- 脑外伤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 脑外伤怎么治疗
- 急性脑外伤外科治疗指南
- 脑外伤可以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
- 高压氧治疗脑外伤效果好
- 脑外伤的治疗方法
- 脑外伤后高压氧治疗的时机选择
- 治疗脑外伤的手段
免费提问